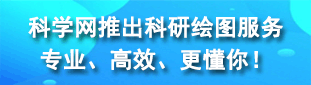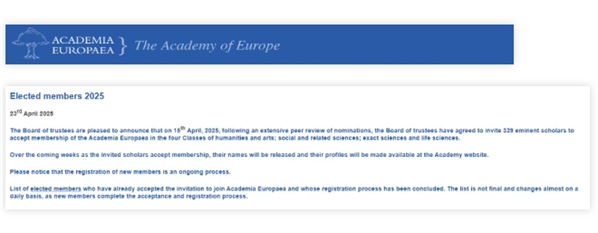端牢中国饭碗,他们一直在路上
“人是铁,饭是钢”,这句俗语道出的是粮食安全这一永恒的命题。饭碗里的事,始终是民之关切、国之大事。如何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、端得更好,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们始终心系的重大课题。
他们当中,有人向盐碱地宣战,让贫瘠的土地焕发生机,变成“新粮仓”;有人深耕种业创新,用“分子设计”育种破解“卡脖子”难题,为粮食生产注入强劲动能;还有人聚焦草牧业发展,探索粮食生产与时代发展的适应特征,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。
从一粒良种到千顷良田,从一片牧场到万家餐桌,他们把责任扛在肩上,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,默默守望着老百姓的一日三餐——让每个人吃得饱、吃得好、吃得健康。
向盐碱地宣战,唤醒沉睡的“粮仓”
1984年,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。这一年起,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徘徊在8000亿斤左右,3年间人口增长却接近5000万。如何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?
1987年,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振声会同农业专家,经过3个月的调研,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农业科技“黄淮海战役”——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。
为找到行之有效的典型方案,李振声和调研团队跑遍黄淮海地区。在河南封丘,调研团队了解到,当地推广中低产田治理措施后,给国家贡献了更多粮食;在安徽蒙城,中低产田的治理成本也都得到了回报。这些实践成果让李振声看到了中低产田治理的可能。
1988年2月,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下,李振声带领400多名科技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,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。1993年,我国粮食年产量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,其中仅黄淮海地区就增产504.8亿斤。
此后多次,每当我国粮食产量徘徊时,李振声都及时敲响警钟:“中国人多地少,粮食安全绝不能掉以轻心!”针对国际上有关“谁来养活中国”的质疑,他的回答掷地有声:“答案只有一个,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!”
2013年,8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向国家相关部门提议,组织实施“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”,对环渤海地区4000万亩中低产田和1000万亩盐碱荒地进行治理。历经5年攻关,该工程使环渤海地区增粮200多亿斤,圆满完成目标任务。
2020年,年近90岁的李振声又向国家提出建设“滨海草带”的设想,以确保我国饲料粮安全。
“国家培养了我,我应该向国家作出回报。”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如是说。他始终把“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”作为毕生追求。
如今,李振声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组建了“滨海草带”青年突击队,集中所内十多个育种和养殖团队的优势科研力量开展攻关,选育耐盐、耐涝的牧草资源,让盐碱地继续释放新“产能”。
抢占“芯片”高地,打造农业发展新引擎
如果说耕地是粮食生产的“命根子”,种子就是农业的“芯片”。进入21世纪,中国农业从“吃饱”向“吃好”转型,种业创新仍然是破题关键。
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。面对老百姓的消费新诉求,以及国际种业的激烈竞争,中国农业发展唯有不断提升育种能力,才能培育出满足市场需求、具有竞争力的作物品种。
然而,传统育种并不知道哪个基因控制哪个性状,只能依靠经验,通过一代代杂交选育出新品种。这使得育种周期往往长达8到10年,且品种间遗传多样性狭窄,越来越难选育出有突破性的优异品种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多次牵头向相关部门提交咨询报告,建议加强种业科技创新,构建国家种业科技创新体系,加快实现高水平种业科技自立自强。
为了推动种业创新,李家洋率先提出“分子设计”育种的理念:“像设计工业产品一样,通过把高产、优质、抗逆的基因模块‘组装’起来,‘设计’出理想的种子。”
这一理念让中国育种从“经验”走向“设计”,也将中国的育种技术理念推向了世界前沿。
如今,从东北稻区到长江中下游稻区,李家洋带领团队“精准设计”的40多个水稻新品种已播撒在我国数千万亩稻田。
分子设计育种还推动了我国育种技术的跨越式发展,为我国生物育种提供了先导性、系统性解决方案。例如,截至2019年,依托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(A类)“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”,来自全国20多家研究单位的200多名科学家采取分子模块设计育种这种新手段,创制了水稻、大豆、小麦、鲤鱼新品系200个,审定新品种27个,并在主产区大面积推广。2025年,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(A类)“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”实施5年再获丰硕成果,共育成37个“一增二减”(增产提质、减投提效、减损促稳)先导型品种,在全国主要农业生产区累计推广6521万亩。
“分子模块设计育种作为一项未来育种技术,不仅能让种子更高产,还能将特殊的优异基因组合起来,定制种子的营养、香味甚至颜色。”李家洋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曾介绍说,比如设计具有高锌、高钙等特殊营养价值的大米,实现营养补给;定制高抗性淀粉大米,从膳食源头预防糖尿病;去掉扁豆里的毒性豆蛋白基因,让扁豆无需久煮就能安心食用。
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,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。未来需要怎样的种子?好种子如何“炼成”?“未来种业”路在何方?
“智能作物的智能培育,是农业科技竞争的制高点。”李家洋在今年3月于海南举行的2025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再次前瞻性地指出。
他解释说,所谓智能作物的智能培育,是指通过发展和使用智能的技术培育智能的品种,从而能够自主应对环境变化,实现“两增两减”的育种目标——增加粮食产量、增强食物食味与营养品质,减少化肥农药等农业资源的使用、减少自然灾害损失。
不过,李家洋表示,新的育种体系需要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,需要建立跨领域的合作模式与机制,因此想要真正实现“智能品种智能培育”的设想,仍需多方面的努力。
如今,担任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的李家洋正在推动国家级种业平台建设,致力于打造智能育种体系。实验室给他分的大办公室他不用,反而把办公用品一股脑地搬到了紧挨着实验室的一间小房间,因为距离课题组近。“我们要紧盯农业科技前沿,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,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”李家洋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曾说。
构建“大粮仓”,草牧业绘就绿色未来
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,过去10余年,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,肉蛋奶等动物蛋白食品的需求激增,饲料粮安全面临挑战,发展畜牧业的传统观念难以为继。
“我国是全球畜牧业第一大国,也是饲料粮需求第一大国。一直以来,我国商业化生产饲草的种源严重依赖进口,饲料安全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曾说。
为了解决饲料粮短缺问题,种康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(以下简称植物所)从2010年起就开始谋划解决之道。
彼时,时任植物所所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在调研时发现,由于不合理的利用,我国约90%的北方草原出现退化,载畜量不断下降,饲料粮依赖进口,生态与经济矛盾突出。
如何解决上述问题?方精云萌生出一个想法:将草地研究与产业需求结合,探索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新路径。他带领团队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“生态草业特区”的构想,并大胆设想“在草原地区建立一个类似深圳特区的改革试验区”。
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,植物所基于在内蒙古的9个野外台站开始尝试改革试验,将天然草地、人工种草、现代化畜牧与生态旅游进行整合,探索牧区发展新模式。
2014年是关键的转折期。经过多年基础研究和小面积试验示范后,方精云带领团队向国务院提交咨询报告,正式提出“草牧业”概念——通过天然草地管理、人工种草获取饲草,经加工后用于畜牧养殖,形成“种草-制草-养畜”的一体化新型生产体系。
长期以来,我国畜牧业存在草畜“两张皮”的困境——种草与养畜两个环节相互脱节,未能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,导致草畜供需失衡。与传统畜牧业相比,“草牧业”突出人工种草、重视草产品加工(保障跨区域、跨季节供应),强调规模化与生态化,旨在构建生态与经济双赢的草-畜体系。
这一理念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肯定。2015年,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写入“加快发展草牧业”,使其从学术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。
“理论走得再远,没有实践就是空中楼阁。”方精云说。2015年3月,植物所牵头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合作,正式启动呼伦贝尔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建设项目。
2020年,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(A类)“创建生态草牧业科技体系”运行,试验规模再次扩大。该专项以植物所为依托,会聚60多家单位的科研骨干,围绕生态草牧业开展系统集成性研究,在内蒙古呼伦贝尔、山东黄河三角洲农高区、云南昭通市设置3个示范点,以期打造生态草牧业产业链科技支撑体系与绿色发展模式,形成成套技术解决方案,推动当地及全国草牧业高质量发展。
如今,生态草牧业理念经过10年实践,已经形成了一套“种草、制草、养畜”的全产业链科技研发创新链条,并为示范区绘制了一张保护粮食安全、服务生态文明的草原“大粮仓”路线图。
“草牧业是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。”种康说,下一步,草牧业发展仍需从单项技术走向系统集成,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广,让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,把科技成果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效益。
为此,种康仍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草牧业基础研究。去年,在他与领域专家的推动下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启动饲草基础生物学专项,依托饲草和牧草全国重点实验室,为饲草基础研究知识的积累提供动力。同时,他还与多位院士专家向中国科学院学部提交咨询报告,建议加速发展盐碱地草牧业,保障国家饲料粮安全,大力推广“以种适地”模式。
“虽然我国作物育种技术较为先进,但饲草产业链仍存在不足,种子企业不够发达,商业化育种体系相对落后。”种康说。他希望基于饲草基础生物学知识和分子设计育种理念,升级换代育种体系,加快培育新型优质饲草,摆脱饲草种源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,牢牢端好中国人的“饭碗”。
“让草原更绿、牛羊更壮、牧民更富、粮食更安,这就是我们的初心。”种康说,他希望用科技之力为我国草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支撑。
| 分享1 |